第三章:中國烽火燒不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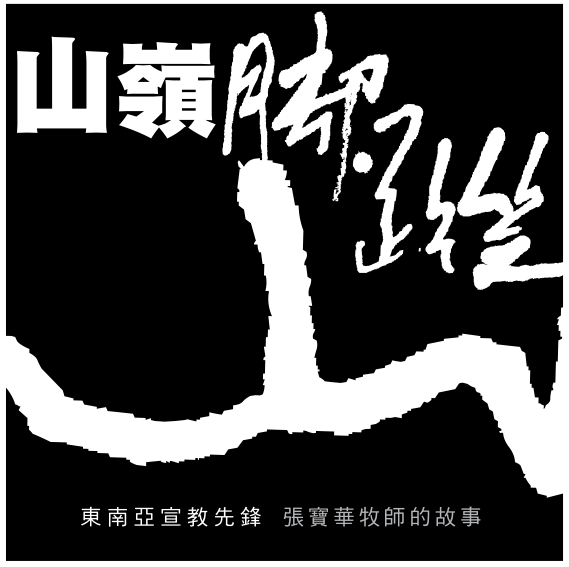
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。
詩篇33:18
1945 年,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,很多人正想安頓一下多年被戰爭徹底打亂的生活步伐,豈知日軍雖走了,但國家並沒有真正的太平。
中國人剛從一場外敵野蠻入侵的浩劫中倖存下來,轉眼就迎來一場更血腥、殘酷的內戰——這場內戰比中國四千年的曲折歷史中任何一次衝突範圍更大、更慘烈。
人民都對戰爭厭倦了,可是,和平快樂的景象卻幻滅了。中國遍地烽煙,共產黨與國民黨雙方激烈廝殺。
離開溫暖的家
1945 年聖誕節前夕,共產黨鐵蹄正朝南方推近,到了滕縣。
「寶安、寶華,你們過來。爸爸有話要對你們說。」張學恭教授神情凝重的將兩個孩子喚來:「這裡的局勢很不穩定,我們也不知道共產黨會怎樣對待我們......寶安已達當兵的年齡,共產黨肯定會訓練你成為士兵,派你去和自己同胞作戰。」張教授實在不想讓孩子參與這場無意義的內戰,甚至可能因此再也沒機會見到他。
「寶華,你雖然衹有十三歲,也未必能逃脫這個危險,所以你們兩兄弟要趕快收拾衣物,明早就立刻起程,逃到寶雲那兒投靠她。」寶雲在南京一家音樂學院教書,而南京還是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下的國家首都。
張學恭教授從來沒有對共產黨存任何幻想。他自己決定留下來,是因為神學院和教會都需要他維持和帶領,不能一走了之,然而他也必須顧慮孩子們的安危。雖然讓年幼的孩子冒著生命危險逃難,實在令父母放心不下,但這也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了。
那晚,張家父母整夜難眠,數著一分一秒......一、二、三,等待破曉。
沒有陽光的黎明終於來臨。霧氣迷濛,兩個孩子拿著小包袱,裡面裝一些替換的衣服、毛毯和食物,寶安先開口說:「爸爸、媽媽,我們要上路了......」聲音禁不住哽咽。
「遇到共產黨巡邏隊時要特別小心。要好好照顧弟弟。」張教授用力抱了抱兒子,簡短的說了一句。
然後,他將目光轉向寶華說:「記得,你是耶穌的精兵,正要衝出敵人的界線......」說到這裡,心中湧起一陣傷感。這孩子與他在屬靈的事上特別有默契,今後卻不曉得還有沒有機會與他分享神的話。
寶華的母親強忍著淚水,緊緊抱著他。她實在不捨得讓才十三歲的孩子在嚴寒之下步行三百公里路,沿途還得到處乞求食物和住處。她用左手摸了摸寶華的褲管說:「記住,媽媽將一個戒指縫在你的襯褲內,你們需要錢買食物時,就賣掉它吧!」
寶華這才發現母親的結婚指環不見了。
「別擔心,我們是將兒子交託給全能的神,衪會保守他們的。」張教授拍拍妻子的肩膀安慰她說:「從這裡到南京,沿途都有我們的朋友照顧他們,妳放心吧!」
張教授帶領家人為寶安、寶華禱告後,母親的淚水終於禁不住,奪眶而出。兩個孩子依依不捨揮別家人,開始踏上一段顛沛流離的冒險生涯。
那一年也是二十年來最冷的冬天。
寶安、寶華兩兄弟沿著中國南下的鐵路跋涉,風夾著雪花狠命地撲打在他們身上,寒氣像鋼針一樣往骨頭縫裏鑽,勞累、饑餓、寒冷相繼襲來。更要命的是,夜幕已經降臨,他們衹能藉著積雪的光亮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沒有人說話,衹有粗重的呼氣聲。
寶華開始希望可以掉轉頭,回到溫暖的家,這一刻他特別想念媽媽。思鄉的愁緒湧起,讓他失去向前奔走的勇氣和動力。
高掛天空的月亮,正冷冷清清地俯視著鋪滿白雪的大地,和那兩個步步艱辛向前走的孩子。
「喂!停下來!要去哪裡?」前面一群士兵用槍攔著他們,其中一個粗聲粗氣的問。
寶華嚇得全身冒冷汗,飢餓的難受此刻完全被恐懼驚慌取代。他張開口,嘗試要回答,但卻怕得發不出一點聲音。八年抗日戰爭之後,許多人早已厭倦了戰爭,眼前這群人或許被逼當兵,很可能會因為一個不耐煩,而胡亂開槍掃射,這樣的事在戰後時有聽聞。戰爭,早已扭曲了人性。
「我們是放假回家的學生,因為沒錢坐火車,所以必需走路。您看,我們沒有武器,衹有幾件衣服。」幸虧寶安鎮定,他邊說邊打開包袱讓士兵們檢查。寶華也不敢怠慢,趕忙跟著哥哥一樣打開了包袱,手卻不受控制的顫抖。
士兵們仍用槍指著他們,一邊檢查包袱,一邊低低的商量,一會兒便擺手說:「你們走吧!」
路程才剛開始不久,就經歷艱險,兩兄弟逃出生天後,不禁在心中默默感謝神的保守。

有一天,兩兄弟發現了前頭一絲光亮,跌跌撞撞向著燈光撲去,茅屋的主人打開門一看,認得寶華,連忙將兩兄弟迎進屋裡,用一些飯菜把他們餵飽。
原來,張學恭教授曾到過這裡傳福音,主人曾見過寶華,因此十分願意向寶安、寶華兩兄弟伸出援手。
主人看兩兄弟鬚髮蓬鬆,衣衫不整,腳上還穿著草鞋,一雙棉襪竟露出腳趾......當即拿出嶄新的布鞋,塞到他們手裏。
寶華張開口想對主人說句什麼,衹見善良的主人忙著端來一盤溫水,在昏暗的燈光下,把他和哥哥的腳浸在水裡,吃力地按摩著,一雙眼睛滿是慈祥與愛憐。那一瞬間,寶華感覺到主人胸懷間的溫熱透過雙腳傳到全身,一直傳到他的心裏。
他突然想起遠在百里之外的父母,一種親人般的溫暖漫過他的心,衹覺得鼻子發酸,喉頭哽咽,說不出話來,淚水順著臉頰大顆大顆地落下......
休息了幾天,寶安、寶華恢復了體力,繼續上路。主人千叮萬囑,這才揮手道別。
風刮在臉上仍然像刀子割一樣疼。但此刻寶安、寶華卻彷彿得到從上頭來的能力,穿著主人送的嶄新布鞋,步伐輕快了許多。

他們有時沿鐵路走,有時走山路,有時是鄉村小徑。沿途遇到不少好心腸的鄉親,借地方給他們住宿,尤其是日戰時期,張教授曾打開神學院,接待無數難民,今天當這兩兄弟來到這些家庭時,他們也很樂意為他們提供蔭庇。有些人甚至還堅持要陪他們走一段路。
若走不到有村莊的地方,他們就在山野過夜,拿出母親挑的兩張毛毯,兩人圍著腳伸進被子睡,但被子太小,還是會冷一個晚上。
逃難途中,耳邊時而會傳來槍聲,有時來自遠處,有時就近在身邊,聽得寶華心驚膽顫。記得有一回,兩兄弟正要搖艇渡河,豈知搖到河中央時,突然聽到一陣槍聲從後面傳來,不清楚是不是共軍巡邏發現他們,也不敢回頭看,心中衹有一個念頭:「要快!要快!快划!」他們拼命划過對岸時,早已精疲力竭了。
那個晚上,寶華作了整晚惡夢,醒來時尚不知身在何處,嚇得全身汗濕。就這樣又折騰了十天,最終抵達了揚子江,隨著一大批難民一同乘汽艇渡江,來到國民黨的地區—南京。
在南京的日子
南京位處華東,長江橫貫南京市,水土肥沃,物產豐富,是漁米之鄉。南京在中國的地理位置很重要,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,佔據南京一帶,多能控制南方,建立政權。然而,南京卻是多災多難的城市,多少政權,多少戰爭,多少烽煙,多少鮮血......歷史的宿命使建政南京的政權多不長久!
「寶安、寶華......」聽到熟悉的聲音,兩兄弟回頭一望,是寶雲。他們暫時安全了。
寶雲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弟弟了,雖然兩人又髒又臭,她還是忍不住緊緊地抱住他們,一邊說:「來了就好,現在沒事了,我們回家吧!」
此時,共產黨軍隊從基層著力,集中拉攏農民、勞工和學生,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,搭配蜂擁而起的學潮,開始在北方與國民黨鬥爭,局勢一片混亂,但是南京暫時尚算安全。寶華在姐姐的安排下,進入初中,搬進宿舍,開始了一段新生活。

內戰期間,實力略勝一籌的國民黨雖然費時費力與共產黨對抗,卻始終沒有收到預想中的效果,共產黨主力依然存在。經過多個月的蘑菇戰,國民黨的軍力、士氣嚴重下降。
1947 年 5 月,共產黨終於取得了戰役的大勝利!國民黨在「孟良崮戰役」中,全軍覆沒,被逼全綫撤退山東。此戰役後來導致國民黨節節敗退和帶來中國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留在滕縣的張家,日子是越來越困難了。張學恭教授抱著極端懷疑的態度,觀察勝利的共產黨領導人如何操縱家庭和社會,限制宗教活動。他知道再繼續留守這裡,也不能起很大的作用了。因此,在寶華離家不到一年,他們全家就在南京團聚了。
一場復興運動崛起
內戰在北方激烈展開,然而到了南京的張家,卻遇上了一個大學界的復興運動。
早在 1937 年,日本侵華戰爭正式爆發,大量青年學生逃難。在苦難與戰爭的陰影之下,離鄉背井的莘莘學子極需要福音的慰藉與信仰的支持,因此大學生的歸主與復興運動在那時悄悄興起。

當時,中國的趙君影牧師(Calvin Chao)於這大時代趁勢而起,帶領這個復興運動,大大影響當時以至日後的大學生福音事工。趙牧師在貴陽富水路開設教會,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前來參加。當時歸主的大學生懷著火熱的心,在校園自行籌組團契,在學校裡舉行祟拜、查經班、祈禱會及傳福音等活動,一片火熱、興旺。
1943 年 4 月,中國基督徒十字軍傳道會(後改名中華傳道會)正式成立。當時來自愛爾蘭的宣教士 Duncan McRobert 及英國來華的宋德成(Fred Savage)向美國西雅圖基督徒商人傳達「華人自傳」的異象——一個中國傳道人向中國人傳道之宣教策略。
在這策略之下,國外基督徒將以經濟直接支持中國人在本土宣教,這可以解決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宣教的很多困難,諸如語言、文化的障礙;簽證的困難;生活的適應及路費的支出。同時也解決了子女的教育問題等。

他們邀請趙君影牧師當監督,在貴陽城設立辦事處,全力支持他推動學生歸主運動。後來更聯同內地會同工艾得理(David Howard Adeney)成立了「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」(簡稱學聯會,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, CIVCF)。
1947 年 7 月,張家落腳南京之際,適逢學聯會舉行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第二屆夏令會,地點位於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國軍烈士遺族學校,約有 350 名學生出席。這也是學聯會最後一次舉辦夏令會,之後中國便落入共產鐵政手中。
「中國從沒有這麼多來自各地的基督徒學生聚在一起聚會過,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聚會」張學恭教授興奮地對妻子及家人說,「當時的聚會明顯看見聖靈在人心的工作......」
這真是一次令人難忘的聚會,各地學生蜂擁而至,有從海路來的,有搭飛機來的,也有坐火車的,十五歲的寶華也參加了這次夏令會,讓他靈命得到挑旺,事奉主的心志更加堅定。
在那值得懷念的數天之中,許多大學生立志不管前途如何,也不管將來有甚麼困難和危險,都願意奉獻一生為主做見證。
在最後一晚的聚會中,學生們爭著作見證,在短短的時間之內,無數參加者見證神對他們的愛,直至深夜聚會才結束。在會中獻身的學生超過一百位。
若按組織存在的時間長短來說,學聯會衹成立了短短不足六年,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,衹算是一個小段落。然而,這段歷史卻記下了中國教會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頁。
許多大學生在這次的屬靈運動得到復興,進入神學院,成為傳道人。這些人以後在面對 1949 年大陸解放的逼迫與苦難,成為各處家庭教會的中堅份子和海外華人教會的領袖。
成立泰東神學院

很快的,張學恭教授也投入了服事南京大學生的行列。他首先牧養一間南京教會,提供一大批年輕人系統及嚴謹的神學裝備,積極培植新一代的教會工人,就像他過去在華北神學院所做的。
同一個時候,中華傳道會(前稱中國基督徒十字軍傳道會)看到要達到培育當地人,使他們能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的宣教策略,便計劃要開辦一間本土化的神學院。其領導人,包括宋德成(Fred Savage)找到張學恭教授,問他:「你願意不願意接受一間神學院院長之職,為主訓練工人?」
「我非常願意。謝謝你們願意給我這個機會。」張教授一口就答應了。神學教育一直是他心中最深的負擔。當年他獨自到美國接受神學裝備,回國後在華北神學院執教,甚至在艱苦的日戰時期,他依然堅持不放棄教導的工作。
他們租了一家舊旅館,成立了泰東神學院。當時不少的大學生信主及靈性得著復興,並且在神學院接受裝備。第一批學員有五十位。
每個週末和假期,張教授會分配學員們深入不同的內地、鄉鎮及偏遠的邊疆宣教。他們用喇叭和手風琴吸引人,然後把福音傳給他們。
張教授有時會帶著少年寶華,隨隊到處宣教。每次他們一起去傳福音時,總會勾起寶華童年在山東和父親一起手牽手到鄉下傳福音的記憶,他心中升起一陣溫暖,兩父子能在經歷了戰亂後,依然同心同行事奉主,他覺得很幸福。
假期過後,神學生們紛紛回到神學院,互相報告、分享:「那天我們去的村莊裡的村民從沒聽過福音,所以村民都覺得很新奇......」
「我們遇到的村民就比較棘手,那些人都不愛聽福音,還放狗追我們......」有趣的、快樂的、傷心的,大家都享受在主裡同心事奉。
張學恭教授除了擔任泰東神學院院長,他也繼續牧養南京黃泥崗教會。雖然局勢不安,國家混亂,但教會在那四、五年內,卻出奇蓬勃發展,紛紛舉行佈道會和奮興會,得救人數再度增加。張學恭教授牧養的教會也越來越多人,最後他們甚至準備建一幢大中央教堂容納不斷加增的聚會人數。
共產鐵蹄一步步逼近
然而,接下來的兩年,共產黨繼續南下,攻陷一城又一城,毫無忌憚地向揚子江推進。南京情勢緊張極了。
戰後的中國在國民黨政府領導之下,慾振乏力。政府官員貪污腐敗,使國家面臨經濟崩潰。當時「奢侈與豪華」似乎是中國國民黨官員特有的生活方式。他們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裡,用轎車接送子女上學;銀行裡的存款大部份屬於官吏們及其親屬。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還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沈沈,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。可以這樣說,共產黨的力量很大程度來自於農民痛恨政府的腐敗和弊政。
在民生問題上,國民黨積累的弊政進一步惡化,通貨膨漲使國家幾乎面臨破產的危機,甚至後來拼命印鈔票也無補於事。人民感到前途黑暗一片,沒有保障。
面臨這種黯淡的前景,大批青年學生不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,倒向共產黨;工商業者承受了沉重的捐稅負擔,也使他們對國民黨政府極度不滿。一時之間內憂外患,國民黨政府漸漸失去了控制能力。
其實,在內戰中,最大的受害者還是老百姓。從 1946 年內戰爆發起,已有成千上萬條生命無辜地犧牲了;中國的幣值像氣溫一樣下降得很快,普通老百姓拿著這些不值錢的紙幣,買不到柴和米,物資又匱乏,千百萬人民饑寒交迫,苦不堪言。
這片飽受戰爭鐵蹄蹂躪的國土,滿目瘡痍,遍地赤貧。街道上到處坐著一堆堆披著破衣爛衫、面黃肌瘦的男人,在靠陽光取暖;有些人身上胡亂裹著幾塊麻袋片,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。路邊不時能看到餓得奄奄一息的人橫七豎八地躺臥著,不知是死是活。
在南京城裡,飢荒逼使勞工們到碼頭去做苦工,賺得一點零錢充飢;未成年的小孩被逼像個奴隸般,站在工廠機器前工作十二至十三個小時,連晚上也得睡在機器下面,賺一點錢幫補家用;婦女和小女孩因為要維持家計,被賣作妾、家奴,甚至下海當妓女的悲慘事蹟時有所聞。若不幸發生罷工事件,中外的工廠頭子會毫不猶疑用高壓手段無情地鎮壓,最後受罪的還是可憐的老百姓。
最冷的冬天
那年冬天,南京空中瀰漫著隱然將至的烽火煙硝味,大家都明白,共產黨拿下南京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自從遼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戰役以後,國民黨的精銳主力部隊幾乎喪失殆盡,其政權正迅速邁向崩潰,共產黨鐵蹄毫不留情地一天一天逼近,南京城深池厚牆已經不足以把戰爭與革命的氣氛摒諸於城外了。
這種氣氛也無可避免地籠罩著基督徒群體中,無論在神學院、教堂、飯桌上,衹要有基督徒聚在一起,大家都會討論共產黨統治下可能會發生的事,卻沒有一個人知道應該怎麼辦。
「我想這是不同的共產黨,應該不像俄國共產黨那樣恨基督徒,要趕盡殺絕吧!」有人會抱著樂觀的心態猜測。
「儘管如此,他們也不會允許神學院和傳道人存在的,或許連去教會都不能呢。」也有人持擔憂的想法。
「共產黨就是共產黨,一個無神的政權肯定容不下有信仰的人,我們再不走,恐怕以後就要祕密聚會了。」悲觀的人會這樣分析,「和西方宣教士有瓜葛的人一定難逃被對付的命運,衹是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對我們......」
「唉!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呀!由他們管國家,應該不會比日本人統治時糟糕吧!」
儘管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,但成千上萬人湧進南京,他們傳述共產黨恐怖的故事,比如拆散家庭、欺壓基督徒、沒收私人土地、強迫人民公社制度、監禁或改造反抗的人......再再加深了人們對未來的無比恐慌。
張學恭教授也有參加討論,不過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。兩年前他曾在滕縣共產黨統治之下,嘗試傳福音卻不果,因此他已打定主意,如果共產黨真的渡江,他們衹好往南方遷移。這次,他不衹要帶自己的家庭,還要帶全部泰東神學院學員一起逃難。未來的中國有許多不可預測的發展,他要爭取每一分每一秒訓練他們,以致真理能堅固這群中國未來的傳道人。

1949 年 4 月 21 日,毛澤東和朱德發出「向全國進軍的命令」。共產黨百萬雄師,在千里長江分三路渡江。當天夜晚,他們按預定部署,在上自九江、下至江陰的千里江防線上,發動渡江戰役。首先自安徽蕪湖西面荻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長江防線,由西南向東南迂迴到南京的側背;同日,突破江陰要塞,對南京形成鉗形攻勢。
4 月 24 日早晨,共產黨先遣部隊直奔「總統府」,把勝利的紅旗插上了蔣介石「總統府」的門樓上。從此,南京這座世界聞名的文化古城,落入共產黨政權手中。
逃難長沙
張家再次跟著無數難民往南方逃。張學恭教授帶著一家十口,和七十個神學生,逃到八百公里外的長沙。
張教授神情凝重地吩咐學生們說:「大家要想辦法在共產黨關閉鐵路之前,搶搭火車,然後我們所有人將在洛杉机聖經學院辦的聖經學校會面。」說完便為大家禱告。隨後,就一刻也不延遲地出發到火車站。
那時還是凌晨,天還未亮,火車站卻早已擠滿了逃難的人。這時候的火車還賣票,但衹有票,卻無座位。張教授一行幾十個人,摸黑搶著有限的位子,努力把自己塞進火車裡。幾個較強健的學生敏捷地先把婦孺們送上火車廂。
早上這列火車出發時,車廂內已經擁擠得水洩不通了。張師母勉強找到一個位子,可是這車廂沒有窗子,大夥喘著粗氣,空氣瀰漫著一股怪味,再加上炎熱的夏天,車廂就像蒸籠,頂難受的。
終於,張教授一行人都安全抵達了。他們住進了湖南聖經學校,並且張教授還可以使用這裡的設施,繼續教導神學。在長沙的九個月,寶華都沒有入學,衹是隨著神學生上課。
1949 年 6 月,共產黨打到長沙,他們再次被迫逃亡。
又一次逃亡
這幾天長沙都在下雨,霉濕的天氣和淒愴、惶惑的逃難生活竟是那麼相像。那段日子清苦得無法想像,一顆心老是懸掛著,流離顛沛的逃難生活,不知哪一天才會結束,叫人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惶然。
長沙火車站和九個月前他們離開的南京火車站沒有多大分別。人群熙熙攘攘,擔的、的、忙著奔逃的,一列列火車擠滿了逃難的人。老老少少,哭哭啼啼,各種嘈雜聲都有。
「我們這樣子逃,一次比一次糟,終於有一天,我遲早走不動。」張學恭教授感到一陣疲倦,不由沉重起來。他努力整頓一下心情,便開始推開人群,想到月臺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們這群人上火車。他最後一次在長沙召集的學生,比在南京的那一批,少了許多。
「走開!走開!這列火車是給政府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坐的,你們等下一列吧!」衹見幾位撤退的國民黨政府軍人守著火車入口處,一邊擋著瘋狂的難民,一邊大聲地說。
難民怒吼著,慘叫著,要打開車廂擠上來。他們用石頭、扁擔、木棒敲打著車廂;有的人睜著血紅的眼睛,對著關閉的玻璃窗咒罵;有的婦女披頭散髮,對著玻璃窗啼哭。
「說不定不會再有另一班火車了。」張教授心想:「我們若不立刻採取行動,可能就別想要離開了。」
張教授迅速回去和其他人會合,對他們說:「你們分成兩三個人一個小組,自己想辦法走。步行的人要儘量避開大路,照顧自己的安全。我們到桂林宣道會及聖經學院會面。」
張教授選了六位最優秀的學生與他同行,他希望在逃亡遷移中仍可以把握時間教導他們。寶華靜靜的聽著父親的吩咐與安排,心中由衷佩服:「就算在這樣困難的時候,爸爸依然不放棄神學的教導,他真是神忠心的僕人。」
「你們都過來。」張教授張開雙臂,好像要將全部人都擁抱在懷裡,他開聲禱告:「求天父保守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平安抵達桂林......」
隨後,大家提著極少的行李,匆匆消失在逃難的人群中。
張教授和家人、學生幾經辛苦,才終於擠進一列車廂裡。月光漸漸明亮了,午夜時分,列車在人海中開動了,離開長沙十多公里,曠野格外寧靜,他們打開了車窗,一股清涼的夜風吹進來,吹走了悶熱的污氣。
然而,沒一會兒,這列車竟然停了下來,衹見前面的列車改換了車頭,他們衹能眼巴巴望著載滿政府和軍人的列車在主鐵軌掠過,而他們卻被留下來了。
唯恐別人擠進他們的車廂,列車停在那裡的一個星期,除了如廁和找尋食物外,他們一步也不離開。就在那一個星期,張教授與學生們在灰暗和窒悶的車廂裡,沒有浪費一刻時間,而是浸霪在學業裡。

寶華身在動亂的革命年代,決定了他的生活動蕩不安。他隨著父母、兄弟姐妹一次又一次逃難,才十七歲的他迅速長大,身體健壯,行動敏捷,甚至可以輕鬆的面對眼前的種種困難。
然而,這一次的逃難,比任何一次都艱難。乘火車逃難的人群擠得水洩不通,連火車頂上坐的都是人,一路上有的人被火車摔了下來,有的被擠死、踩死,帶的行李也丟失殆盡,情景慘不忍睹。
寶華好不容易擠進火車,想找一個位置。他想到家人,人那麼多,都不知道他們在哪裡,是不是已經上了列車?衹見火車頭放煤氣處有個小空檔,他正考慮可以不可以擠進那個位子。
「小子,你想睡這裡要給錢。」一個火車駕駛員粗聲粗氣地說。
寶華趕緊手忙腳亂地從口袋掏出僅有的錢交給他,終於能蜷縮在這小空間裡。早就聽說在車廂裡,有錢的就比較容易辦事。這里完全是生命與金錢的比賽,鈔票像蜂蝶似的滿站飛,眼淚與血汗像雨水似的到處落!
這時列車停在其中一站,工作人員紛紛換班,剛換上來的駕駛員看見寶華,開口對他說:「喂!你坐這裡是要付錢的」
「我已經付過了。剛才那位駕駛員已收了我的錢。」寶華理所當然的說。
駕駛員大聲地咆哮:「現在歸我管了,你要坐嗎?要就付錢,不然你就給我下車!」
寶華剛才已把僅有的錢都交給第一個駕駛員,哪裡還有錢?他衹好下車。火車就快開動了,他的心真著急,萬一掉了隊,就見不到家人了。他瘋狂的挨著月臺跑,要看還有沒有可以擠進去的車廂。但火車上的人是無法想像的多,火車頂棚上坐滿了人,車輪軸承間架起木板,上面也睡了人;車廂與車廂之間,也站滿了人。車廂內更不用說了。
這時他聽見一陣凄慘的哭聲,目光不自覺掃過去,衹見一位婦女,帶著三個小孩子,她懷裡抱了一個吃奶的孩子,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挨著她一邊一個。
婦女淚眼婆娑向過路的人求助:「他們的爸爸在路途中病死了,我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真不知道該怎麼辦,請過路人幫助一點......」她那樣子好可憐,寶華多年受父親的影響,很想幫助她們,但他口袋一點錢也沒有,還能做什麼呢?
「鳴!鳴!鳴!」哨子響了,火車快開動了。寶華這才想起自己還沒上到火車,心一急,突然有人一把拉著他的手臂,他順勢縱身一跳,就站在火車最後一個梯級上。他定了定神,才發覺把他拉上來的是他父親的一位學生,王先生。
隨著轟隆一聲巨響,火車開動了。聽說這是最後一趟南下的火車了。
寶華和王先生拉著梯子的扶手,身子懸掛在車廂外面,火車速度加快了,他擔心萬一鬆手,掉進鐵軌,就要粉身碎骨,因此抓得緊緊的。列車正飛馳在青山綠水間,金黃色的稻田散發著稻香,這麼美麗的景色,寶華卻無暇欣賞。此時凜冽的寒風好像要撕裂他的皮膚、煤屑擊痛他的臉。衹要列車稍為抖動,他就有掉下車的危險。
「別擔心,我的包袱裡有繩子,待會到達下一站時,我們可以用來綁著自己在梯子上過夜!」王先生用足於蓋過火車輪子吵聲的聲量對寶華高喊。
在這漫長的逃難線上,寶華和王先生咬緊牙根,頂著寒風雨打、艱辛困頓、忍飢耐寒......一路的危險,使他們的神經繃緊。
火車仍在疾風中前進。
晚上,兩人要輪流守候,讓另一個人可以休息。每當睡著的人快要滑下來時,另一人就要馬上擰他一把,讓他清醒過來。
長沙離開桂林衹有四百公里,但這列火車卻繞道走了更長的路。火車常常停下來,有時是讓路給軍用的火車;有時是火車駕駛員要和供應煤和水的人交涉;更多時候是他們要向乘客勒索更多錢。
有一天,當火車在軌道高速飛駛時,寶華依然擠在車廂外的樓梯上,拉著扶手,向對面的一排正在開動的列車望去,衹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婦女,也和他一樣懸掛在車外,那列火車為了搶道加速開出站臺。寶華正為那位婦女提心吊膽,如果掉下來,就會捲進車軌,他希望有個善心的人在車上拉她一把。說時遲那時快,就在一瞬間,她鬆手了,掉下車軌......
這一幕牢牢佔據著寶華的腦海,使他徹底失去了勇氣。一路上,他不斷看見屍體,有時是一具,有時是幾具。屍體旁蒼蠅成群,其臭無比。死亡和痛苦重重環繞著他,每一列載著難民的火車,似乎都有說不完的死亡悲慘故事。
王先生努力振作寶華的意志,他們唱詩、背經文,讚美神保守他們至今仍平安。當天氣放晴,一縷耀目的陽光照亮了大地,寶華背起了詩篇:「我要向山舉目,我的幫助從何而來?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。」他心中有一股深深的平安。他感覺到神與他同在,也知道父母正在為他禱告。

行程的最後一段時間,真是一個噩夢。列車不知何故停在一個車站。當晚下了一場豪雨,寶華和王先生飢寒交迫,身上卻沒有分毫。其實,有也未必有用,因為物資匱乏,食物的價格早已超過一般人能力可以負擔了。而且,就算有錢或食物,也會被逃兵們搶去。
車站擠滿了逃難的人群,一天、兩天的等待著列車的到來。吃、喝、拉、睡都在這個地方,一段時間下來,這已經不是車站,而是「糞坑」了!可誰也不離開這「糞坑」,恐怕離開這兒,便沒有上火車的機會了。
寶華和王先生忍受著飢餓,衹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地方,好好睡幾個小時,他們已經有好幾晚沒有安心瞌眼休息了。最後,他們和十多人一塊擠到車站內一個陰濕角落。地面鏽跡斑斑,周圍陰沉沉的,空氣污濁,他們衹好勉為其難地坐臥。
好不容易煎熬了兩、三日,火車總算又開動,寶華和王先生立即馬不停蹄地擠上火車,奔赴桂林。火車走了一天一夜,一路艱辛困頓,風餐露宿,忍飢耐寒,在他們安全抵達桂林時,終告結束。

寶華在逃難的日子裡,看盡人生醜態,每個人都自己顧自己,不理別人的死活。搶、騙、偷、打......各種劣行,成了流離顛沛的生活中,最寫實的一面。
親眼目睹人性陰暗的一面,令寶華的思想不斷受到衝擊。他不時想起父親自幼的教導:「不要單顧自己的事,也要顧別人的事」又想起父親曾說:「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,就是作在我身上了......」他還記得,父親說當他幫助人時,其實就是一種敬拜的行動。
這些話在苦難中,格外鮮明;這段苦不堪言的逃難經歷,也讓寶華對神的話有另一番深刻的體驗。
另一個開始
抵達桂林宣道會不久,張學恭教授便立刻著手重新開辦神學院。聖經學院答應暫時將第二樓借給他們上課,因此很快的,張教授召集了他的學生,繼續教導神學。
寶華的母親在最貧困的環境,仍然堅持奉獻。她用一生積蓄買了一塊地,建設一座神學院。他們沒有任何資助,衹好在路邊設地攤,變賣母親的珠寶手飾、舊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具,一點一滴籌足經費。
寶華每天陪著母親坐在地攤上,看著他們家僅有的財物,慢慢的一點一點消逝,他也一點一點的明白了母親對神的愛。
共產黨的陰影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的生活。毛澤東的軍隊不斷向南方迫近,國民黨聞風喪膽,一路往南部撤退。明顯的,共產黨遲早必然控制全中國已成定局。
張學恭教授再次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。他召開了一個嚴肅的家庭會議。寶華緊張的挨著姐姐和弟弟坐下,心想:「我們已經三次逃離共產黨的手,這次爸爸會不會又提出另一次逃亡?」想到這裡,他心中不禁一顫,在長沙的苦況如今還歷歷在目;父母年紀老邁,不知是否還承受得了逃難的折騰。
「我們不再逃亡了。」父親彷彿知道寶華想什麼,「我和媽媽及已婚的哥哥、姐姐討論過,我們決定要留下來。」
「但是寶雲要帶五弟寶義到臺灣,投靠已經在那裡的大哥寶誠......」
「那我呢?我要去哪裡?」寶華想。
父親很快就解答了寶華的猜測,「寶華,你是一個敏感神話語的孩子,也很熱心事奉主,爸爸希望你能先到香港繼續唸書,將來能讓神使用。」父親的語調既溫柔,又充滿權威,寶華很自然地便點頭順從父親的安排。
「爸爸會聯絡中華傳道會的主任宋德成和其他人照顧你。」
「我一個人去嗎?」寶華還是有點不放心。
「寶雲和寶義會先送你到香港,然後他們才到臺灣找寶誠。」
這時,母親緊緊握著寶華的手,輕輕地問:「記得你從山東去南京時,媽媽縫在你褲子內的戒指嗎?二姐要結婚啦,就給她吧......」說到這裡,媽媽的眼睛紅了,眼淚在眼眶裡打轉。
她轉過身來,背著孩子們說了一句:「你們在外頭要注意身體啊!」然後,寶華聽到媽媽哽咽的聲音。

從 1949 年 4 月,當共產黨軍隊渡過長江攻下南京的時候,國民黨的統治實際上已邁向滅亡。殘存的國民黨政府後來逃到廣州,企圖負隅頑抗。豈知沒多久,共產黨沿粵漢路兩側南下,佔領韶關,直取廣州。隨後,共產黨繼續佔領清遠、花縣、從化、增城,左路逼近博羅。廣州的東、北、西三面都處在共產黨的包圍中。
終於,在共產黨強大攻勢下,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和行政官員等人被逼逃到臺灣。接下來的日子,中國引起一陣大疏散,國民黨軍人、逃兵和許多不願參戰的人民,紛紛沿東南西北逃竄到緬甸、遼國、泰國邊境、臺灣和香港等地。
10 月 1 日,三十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,「中國人民站起來了!」毛澤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。這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。
離別
就在國民黨全盤失敗的前兩個月,寶雲、寶義和寶華三人辛酸的與父母和兄姐們話別,向香港出發。
從廣州到香港的路途出奇的平靜,一點也不像寶華以往的逃難經歷。然而,寶華的心卻一點也不平靜,此刻他對未來充滿惆悵,對前途也感到無限哀嘆。他不停回想離家時那一幕,爸爸媽媽的哽咽聲裡包含多少牽掛、關心和不捨,思鄉之情油然升起,眼淚忍不住便淌下。當時,寶華並不知道,這次的離別,竟是他與最敬佩的父親永別了。
當寶雲、寶義和寶華三人扺達香港時,意味著寶華既將要揮別摯愛的姐姐和弟弟了。到香港的旅途中,一路上三兄弟姐妹說了不少話,大家深深感到,昔日同唱聖詩於一堂,今天各奔東西,天各一方,不知何日才會有相聚的一天。
分別時間臨到,寶華衹能對姐姐和弟弟說一句:「再見」,嗓子便哽咽起來,別離的悲傷再度刻劃在寶華的內心。
當他們分離時,寶華將母親的戒指交給寶雲,而他自己珍藏了一個寶貝—他留下了父親那本《個人佈道》的著作,希望有一天能在香港出版。